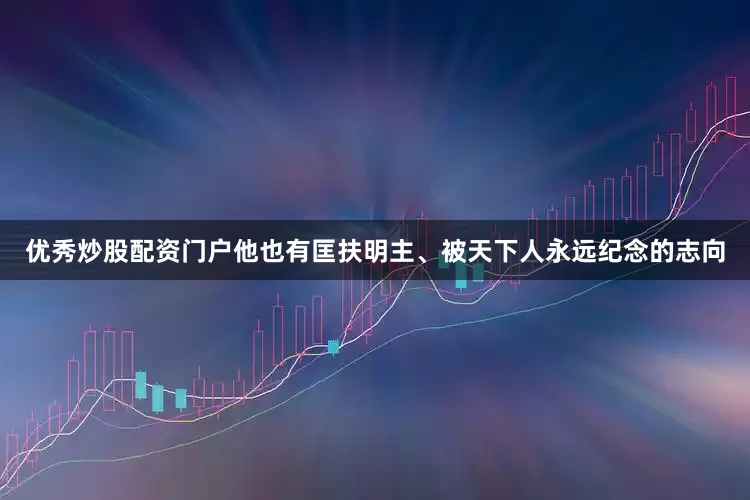
图片
长江水奔流至瞿塘峡时,江面上忽立起两个百丈高的山崖,左曰赤甲,右曰白盐,好似两扇石做的门,只留一道窄急不到百米的隙缝,江水侧身急过,自此一泻千里。
这万夫莫开的险境,就是古夔州所在。
大历元年(766年)春,杜甫从卧病数月的云安抵达夔州。
彼时,他的至交好友几乎都离世了,剩下他,似天地间一只倦飞的沙鸥,暂栖在古老而荒僻的夔州。
图片
清 丁观鹏 杜甫诗意图局部那时候他还不知道,他将在夔州写下240多首诗(占他一生的三分之一),他平生的巅峰之作《秋兴八首》和《登高》,都属于夔州!
但困于夔州的两年里,他始终都想离开。
初到夔州,杜甫住在城西郊一个山腰里,他在诗里把这个租来的房子叫作“客堂”,“山腰宅”,为了贴补生计和治他的风湿症,他在山腰宅养了上百只乌骨鸡,大概这些个鸡脚力甚健,天天喧呼籍踏,在几案上跳上跳下,后来实在太闹腾了,老杜只得催促大儿子宗文给鸡做个高点的栅栏,求得人鸡两清静。
不必与鸡为伍的清闲里,他也会经常出去走一走,去白帝城,去武侯庙,去滟预堆,去八阵图。归来,他总是有更多的感慨。孔明死的时候54岁,他如今已55岁了,他也有匡扶明主、被天下人永远纪念的志向,但他的现实,却是在远离长安的夔州,管理一百多只鸡……“闻道长安似弈棋,百年世事不胜悲”(《秋兴八首》其四选句)。他喃喃自语,常常从白天坐到薄暮,又坐到深夜,至天光发亮时,仍然无寐。他对整个夔州都不满意。在他看来,这里的人愚昧、迷信、不好打交道,风俗也不像话,竟然让女人上山背柴,男人就在家坐着,也不爱读书,宁可冒死贩私盐、跟着商船在浪头里打滚,自己跟他们,简直是鸡同鸭讲的不通……夔州还有老虎,常常趁黄昏时下山来散个步,和老虎一样恶的还有当地的青皮无赖,如此穷山、恶水、刁民,搞得他“晚上要防老虎,白天要防刁民”……吃的喝的他也不适应。夔州多是石山,种不了多少庄稼蔬菜,就是近水,多的是鱼鲜,夔人惯了吃鱼,家家养乌鬼, 顿顿食黄鱼,家常餐桌上还有一种叫“白小”的鱼,夔人把它当作小菜——但杜甫天生讨厌鱼腥,让他天天吃,顿顿食,这如何受得了!大历二年(767年)三月,早前从“客堂”搬至西阁,却与“刁民房东”相处不睦的杜甫带着家人,又离开西阁,搬到了赤甲住。赤甲虽然更为荒僻,却颇为清幽。更妙的是,夔州都督柏茂琳帮他买得瀼西四十亩果园和草屋数间,又帮他租到东屯一部分公田,于是三四月间,为了赶上春耕时节,杜甫再次搬家,从赤甲搬到了瀼西。大历二年(767年)八月,杜甫再从瀼西移居东屯,这是他在夔州的第五个居所,也是在夔州最后的居所——四个月后,他将告别这个困居两载、他不得已停留的所在。整个夔州的两年,他一直都想离开——他太孤独了。和兄弟们的长久分离,与中原迥异的夔州风土,愈来愈折磨着既老又病的他,这归心一起,便不可遏制。早在暮春时,杜甫曾收到弟弟杜观的书信,说已在江陵,预计月末将到夔州,杜甫欣喜若狂,入夏,因杜观要去蓝田迎新妇,杜甫又送弟北归,短暂相聚却相别,杜甫殷殷叮嘱——记得要快去快回,秋天的时候好归来一起喝酒。但不知怎么,这年重阳,杜观并没有回到夔州,杜甫独酌杯酒,抱病登上白帝城外的高台,不胜萧然。风急天高猿啸哀,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,潦倒新停浊酒杯。——杜甫《登高》图片
清 董邦达 杜甫诗意轴局部三个月后,大历三年(768年)的正月,杜甫把瀼西果园四十亩送给友人南卿,随后带着家人从夔州出峡,前往江陵。之后的两年,他漂流于江陵、公安、长沙、潭州,最后决心溯湘江北上长安,却病逝于北上的湘江船中。他始终没能再回到长安,但他也许庆幸离开了夔州——只是,他诸多名篇里世人记得最切的,正是他在夔州写下的《秋兴八首》和《登高》,明人胡应麟甚至认为,《登高》堪称古今七律第一名,自带超越万载千年的光芒——“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,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。”也许,这夔州就是他命里的烙印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烙印,只是常不自知。作者:任淡如
本文为菊斋原创重发。公号转载请联系我们开白授权。
▼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配资网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